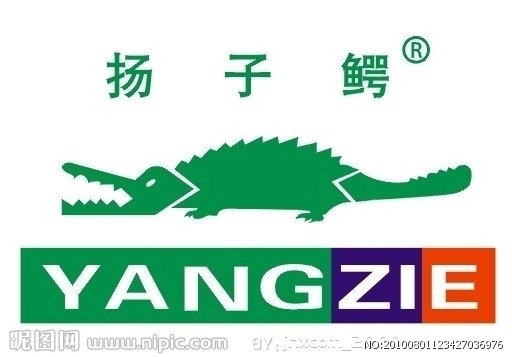近日,林剑在时堂收到了服装品牌素然(ZUCZUG) CEO黄志峰的简讯。一条“祝贺简讯”,黄志峰说,“时堂的产品越来越适应市场了”。“时堂”是上海时装周期间的一个短期展会,你可以笼统地叫它showroom,但更准确的说法是trade show。从2014年4月开始,时堂连续举办了三季,时装评论人林剑是联合创始人之一,他基本复制了国外showroom的形态:时装周期间,设计师品牌在showroom参展,吸引买手前来攀谈订货。

林剑乐于跟我们分享这条简讯是因为,由王一扬创立于2002年的“素然”是中国最早的设计师品牌之一,现在主流商场里都是“素然”的门店——它成功了。《华尔街日报》曾撰文说,王一扬一直“是一位兼具商业头脑的设计师”。包括时堂、Ontimeshow在内的showroom,希望在更多设计师品牌身上复制这种商业成功,他们的方式是搭建一个聚集设计师品牌和买手的线下交易平台:品牌方有机会解释自己的服饰作品,买手可以在一个高密度的空间里找到适合的产品,并亲自触摸面料,这和在T台两侧观看走秀的感觉完全不同。
这一季上海时装周期间,时堂、DFO、Ontimeshow、FDC、VDS、T的n次方等showroom都吸引了不少人。上海时装周主办方也加入其中,首次设立官方展会“MODE上海”,邀请多家showroom加入。主办方称,希望“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买手及行业人士搭建一个促进商贸对接与合作的商业平台”。
人们开始去思考时尚产业中“钱”的流动,原因之一是中国的设计师群体变得前所未有的满。在王一扬和马可之后,先是2008年杜扬与周翔宇(Xander Zhou)的名字出现在当年的英国潮流杂志 Dazed & Confused上。王汁(Uma Wang)、王海震(Haizhen Wang)、张娜(Fake Natoo)、李鸿雁(Helen Lee)、王在实(Vega Wang)等人紧随其后,登上了各种时尚杂志,其中很多是中文杂志。
现在,他们的名字都被记录在一本由英国人新撰写的书籍Fashion China里,但这本书并没有提及他们是否在各自的市场中实现了盈利。在我们上周对王海震的采访中,王海震称他创立了5年的品牌刚刚取得收支平衡。这还是在他获Fashion Fringe奖项,名声大噪并得到赞助之后发生的事。
事实上,他们很有希望赚钱。因为这个市场变化太快,那些习惯消费大牌的人很快就有了消费设计师品牌的需求。“我们当时在时尚杂志上看到了设计师的衣服,但是我们买不到。”“栋梁”主理人之一Tasha说,为了能够买到衣服,她在2009年参与创办了栋梁,一家多设计师品牌集成店,由买手挑货,也叫“买手店”。根据地产咨询机构睿意德联合观潮网发布的2015年统计数据,全国有近300家买手店。

目前来看,最能帮设计师赚钱的还是买手,至少他们愿意出售这些风格和价位都不那么容易接近的服饰。在今年的Ontimeshow上,Tasha带着洛杉矶买手店H.LORENZO创始人Lorenzo Hadar一齐对媒体说:“跟设计师相比,买手更像是创造潮流的人,不是设计师在讲故事,而是买手把不同的品牌放在一起,一起给消费者讲故事。”
这些故事能够为品牌带来影响力,并最终把影响力变成销量。2011年,连卡佛在北京和香港投放了Valentino的“摇滚明星”鞋之后,顾客排起了长龙。在两年前的一次采访中,林剑赞许连卡佛善于在“吸收国际上重要设计师的作品”与“挑选出最实用的货品”之间保持平衡。换句话说,他们了解设计师,也了解市场。
就是这样,买手店希望成为下一个连卡佛,设计师们渴望成为下一个Valentino。Showroom打算介绍他们互相认识。
什么样的场景适合品牌跟买手相遇?尽管受到一些质疑,林剑和他的合伙人杨炯还是认为,时堂设置了一个不错的场景。它是一个更开放的短期展会(trade show),各类品牌都可以付费参加,而不是常年展的showroom,后者比如DFO展出的大部分品牌由自己常年代理。“我们要做包容性的东西。”时堂最早是这样说的。上一季结束后,人们抱怨这个乐于包容的展会一团乱。
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时堂称,一年半之后,时堂已经成了买手们最明智的选择。因为他们对品牌风格进行了筛选,筛选率在50%-60%。除了品牌的资质,这主要基于对当下设计师消费市场的判断,即使是刚开店的新手,在这里选货也基本不会有大错。
杨炯相信,60%-65%在时堂展出的品牌风格适应于主流消费市场。这个消费市场的主力客群是林剑所谓的“以前穿LV的人”。另一家showroom“T的n次方”的创始人朱卫明、成都肆合买手店的创始人蒋昊和FAKE NATOO的设计师张娜对主力客群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还有超过30%的品牌用来测试的新风格,自然地,他们通过展会完成的订单数可能不尽如人意。设计师Yili 2014年10月带着她在伦敦创立不久的女装品牌参加了时堂。她发现,重要的买手仍然喜欢前往知名品牌的展位,而Yili即使在展会结束后也只收到了少数几家买手店的合作意向。
时堂在2014年11月发布的公开数据显示,上一季时堂完成的订货总额在7700至9000万人民币。但一家来自英国的代理式showroom(Project Crossover)和台湾设计师品牌Daniel Wong都表示,他们对这个数字的来源抱有怀疑。后者在时堂结束后,又在另一间常年展showroom “DFO”设立了展位。基于做常年展的经验,DFO配有专门的人员,为买手介绍参展的品牌,无需品牌方操心。

对展会促成订单的多少,林剑回应说,山本耀司的副线Y’s上一季在一小时内就完成了二三十万的订单。时堂已成为Y’s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代理商。“而有些品牌不成熟。”林剑说,他们应该把参加showroom当作商业实习,在买手的拒绝中获得实战经验,并借此机会敦促自己按时完成新一季的产品。
这样说来,参加展会为品牌带来的实际效益确实不一而足。展会主办方能做的大概就是提供“面上”更好的服务。比如灯光、装潢、网络以及更全面的信息反馈。另一场展会Ontimeshow在结束后将继续收集品牌方和买手店的反馈。创始人顾叶丽说,这会花很多时间,但收集的方式比较随意,和订单量一样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设计师还希望有一个面积稍大的独立展位,可以展示尽量完整的产品线。由于场地限制,这通常很难实现,比如这一季的“MODE上海”。参与联合展出的showroom “Alter”和“DFO”都只象征性地展出了一些具有辨识度的搭配,而大力宣传自己的常年展所在地。
Ontimeshow的创始人顾叶丽从第一季开始就尝试做全开放式的展位,没有任何隔断。这同时也能有效地利用展示面积。“从买家来说,浏览的愉悦程度会非常高,每个角度都很清晰。”顾叶丽说,在办展之外,她是一家影视公司的艺术总监。一位希望匿名的资深买手表示,Ontimeshow的品牌组合和规模大小都很舒服,但他更喜欢时堂有隔断的设计,这样更方便和品牌方交流。带有隔断的品牌展位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在保证服务的前提下减少租金或服务费是另一种办法。Both showroom本打算今年入驻时堂,但因为收费太高选择了“MODE上海”。时堂参展方香港Match showroom的负责人雷云称,时堂国际场的展位费是香港时装周同期展会的4-6倍,但她并未感到在服务上有何出众,反倒在基础设施上有些糟糕。
今年新出现的展会“T的n次方”免费向设计师品牌开放,不少上一季在时堂参展的品牌都搬去了那里(两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新天地企业天地3号楼,新天地对两者都提供了免费的场地赞助)。创始人朱卫明说,当他向设计师Masha Ma发出邀请时,Masha Ma表达了遗憾,“为什么不早说,都签时堂了。”朱卫明转述道。
设计师们需要意识到,在市场上,通常都是终端的需求说了算。因此,尽管showroom向他们收取费用,但仍然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买手。时堂以此来解释他们的高收费,这些费用可能无法直接反映在对品牌的服务上,而是用于对买手的培训。在5月份,他们将会提供免费的为期二十多天的买手课程。“相对来讲,最重要的客户是买手,不是品牌。”林剑说。
DFO创始人叶琪峥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showroom也好,trade show也好,买手的质量和数量是核心竞争力。”
一个有趣的悖论是,厉害的买手可能没那么需要showroom这个环节的存在,厉害的设计师也一样。
成都买手店“肆合”创始人蒋昊来到上海的行程是这样的:第一天看秀,第二天拜访设计师的工作室或showroom,结束之后再逛逛各式showroom,看看新品牌,也看看这个在中国的新兴行业发展状况如何。但和国外的大部分买手一样,他不会马上下单,前者甚至要观察一年才会下单。
如果没有附加服务,这种传统展会模式会遇到挑战。至少,它在信息沟通上的必要性已经因为互联网大大减弱了。较从前,设计师有更多的渠道找到买手店的联系方式,他们随时可以发去一封电邮,并附上自己的lookbook。最多的时候,蒋昊一天收到了8封设计师的自荐电邮。创立于2010年春季的北京买手店“吾号”,在2013年年底之前隐藏在胡同里的四合院内,之后以举办临时售卖(pop up shop)为主,也经历了一个从“吾号找设计师”到“设计师找吾号”的过程,“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品牌及设计师会主动联系我们希望合作。”创始人Virginie Kompalitch说。

吾号
另一方面,即使参加展会,双方的对接也经常会跳过展会主办方,由品牌和买手提前完成。Match Showroom和project crossover 邀请了自己的主要客户,而不是依赖主办方时堂。杨炯称,时堂确实没有向任何买手发出正式邀请,而是采取注册的形式。尽管雷云略有不满,但她也很清楚,这更多像是借着时装周的一次客户聚会。project crossovers的创始人陈容则说:“需要让客户看到我们在保持品牌活跃度。”
更成熟的设计师喜欢单独开设showroom,尽管他们也会出现在展会上。薄荷糯米葱(BNC)的买手曾思禹特地去时堂看班晓雪的作品,但他表示,不会在时堂下班晓雪的订单,而会选择去班晓雪在广州的showroom——那里有班晓雪作品的全系列。王海震选择在时堂国际场结束后,在永嘉路设立为期4天个人showroom,他认为第二种方式能带来更多有效人流。
理论上来说,个人showroom更多地用于老客户的维系以及订单的追踪,大型展会则会让品牌接触到更多新面孔。两者相互补充。但问题是,值得认识的好买手并不多。除了声名在外的几家买手店,设计师很难通过一次展会就了解这些四处散落的新渠道对品牌到底意味着什么。
Business of Fashion的创始人Imran Amed指出了设计师需要了解买手店的哪些特质:清晰的客户群,水准、风格相符的其他品牌,买手店在销售之外提供的服务,以及买手店会保证支付。这些资讯都在展会之外。如果不去了解,“还是等于在批发”,朱卫明说。只要想象一下上海的七浦路或者北京的动物园,设计师就会意识到,任何一个不小心就让品牌掉价。
对成长中的买手,展会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showroom(展会)是面向刚起来的买手店,而非成熟的买手店。”栋梁创始人Tasha说。杨炯估计,加上这些新兴的买手店,中国的买手店有1000多家,而他的微信上就有600多个联系方式。他们需要获取更多的品牌信息,showroom是个不错的方式,它最大的好处是能密集地提供产品实物,而设计师通常“求贤若渴”。
栋梁和国内的showroom合作很少,作为最早一批发展起来的买手店,他们比国内的showroom更早就认识了设计师。为了跟进新锐设计师、特别是在海外创立品牌的华人设计师的最新动向,栋梁通常在巴黎完成订单。这一时间会早于上海时装周的4月和10月。

栋梁
上上季,栋梁带着6位合作设计师在上海时装周期间单独举办了“栋梁一日”。今年5月,栋梁会带着自己店里的几个设计师品牌到洛杉矶买手店H.LORENZO做Pop up shop。连卡佛也在创立一个showroom之外的平台。5月,连卡佛将会在香港和上海,分别举办一次“开放日”,设计师们可以带着自己的作品,到这两个地点和连卡佛的买手及创意团队见面。
对刚起步的设计师品牌,如果你想要找一份“商业实习”,showroom也不是唯一的选择。成熟的买手店也可以作为“试验场”。薄荷糯米葱和栋梁都在发掘新锐设计师,从毕业前做第一个collection 开始就在店铺呈现,他们可以在市场反馈中找到自己需要提高的东西和不足。当然,这是件高门槛的事。“每年我们只能是全力以赴地推荐一到两位新人,就像个whole package 。”Tasha说。而如果只是扣点而非买货的“寄卖”产品,确实要容易得多,但买手店一般不会给予更多的助推。
通过showroom积累市场经验的一个优势是:showroom面对全国,而买手店有区域性,这可能会让设计师品牌错失远方的机会。“买手店要看店在哪里,showroom是看整个中国。”Alter showroom运营经理贺雅克(Jac van den Heuvel)说。Alter同时是一家在上海运营了5年的买手店,但贺雅克表示,Alter在店铺里出售的品牌和showroom代理的品牌不完全重叠。
“T的n次方”的创办者朱卫明试图完成一种新奇的对接,带着设计师偏离“设计师—showroom—买手店”的轨道——如果他能成功的话。“买手店还是少,设计不一定要进买手店。”朱卫明说。朱卫明做皮革出身。尽管2014年9月在新天地时尚开设了第一家买手店“N的n次方”,但他更大的兴趣在解决设计师的生产问题,并把设计师产品送入商业产品的分销渠道。

T的n次方
Christophe Terzian实现了这两点。今年由“N的n次方”代理的法国设计师品牌Christophe Terzian于4月10日在新天地走秀。去年,这个品牌主要在商业品牌店、精品店销售,朱卫明旗下的皮革公司为其提供面料和工艺。
朱卫明希望通过“T的n次方”找到更多的“克里斯多夫”。他没有向设计师收取租金或服务费,采取了通常用于常年展的“交易提成”模式,但最终证明,这种深度合作不适用于短期展会。“(我听到)有设计师说,如果你不跟他们(T的n次方)走,我给你10%折扣。”朱卫明说,他本来打算在后续跟进,解决设计师的生产问题。如果合作愉快,再连同设计师开发新品牌或者贴牌,做精品批发。
这是一个让时尚圈听起来“悲喜参半”的计划。我们当然知道,时尚不再“只管好看,不管难受,只管消费,不管生产”。生产是个受到普遍承认的问题环节。在此前和叶琪峥的采访中,他指出了国内设计师品牌的三个问题:定价高,折扣高,起订量高。叶琪峥解释说:“这也和国内的供应链有关系,工厂一般只接大单子,这个只能靠设计师自己去想了。”
根据朱卫明的说法,他的皮革工厂和意大利面料商伙伴此前为Gucci、Amarni和Chanel服务,现在正帮助超过十位设计师做衣服,每个人不过定一两件(对订单数量没有要求),并参与张娜等设计师的成衣制作。他还提到Masha Ma参观了他在海宁的工厂,“她觉得这样合作,做设计师才有意思”。在展会上,朱卫明展出了面料。“让设计师对面料有概念,这很重要。”朱卫明说
从上游的优势上来说,朱卫明是背景有点像买手店Seven Days的主理人张龙江。张龙江从1991年开始做面料生意,也为国际品牌供应面料。2008 年,他正式并购了香港的Seven Days。但“N的n次方”没有Seven Days可以参照,朱卫明的经验来自商业化程度极高的精品店。这很可能会让设计师矫枉过正。
在“T的n次方”上,朱卫明邀请的客户几乎全部来自品牌公司、高端精品店和欧货店。这些人的起订量通常在200万以上,因为海外品牌的精品店效益下降,他们急切地想要转型成为买手店。但很可能,他们对买手店的理解和朱卫明一样:“装修更凹造型”,并且以销售业绩来决定陈列衣架的杆数,而非想着怎么完整地展现品牌系列。
如果是这样,这个新生的showroom对设计师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幸事。他们得重新想想Imran说的那三条建议:客户群、品牌群和服务——至于保证支付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
这个时尚界的商业老师还教导年轻的设计师说:“建立、发展品牌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五年、十年都是短暂的,要有耐心,不要急于一时,设计只是时装中的一环,要将设计从二维变成三维的,都不是仅仅用设计就能完成的,加强作品的完整度,提高产能,小心地一步一步地慢慢发展起来。”
这段话应该也适用于整个时尚产业。